从日本企业身上,学什么和怎么学?
日本对于很多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当我们从企业经营的切口观察日本,会得到别样的视角。2025年上半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苏锡嘉教授跟随中欧创投营组织的游学团去往日本东京和名古屋进行了5天的访问。其间,他们参访了若干日本知名企业,并与日本学者和企业家们进行了分享交流。虽行程匆匆,但苏教授深受触动,将诸多所观所感整理成文,也在中欧首推的【中欧特色课】视频节目之“海外游学篇”中精彩呈现,干货满满,充满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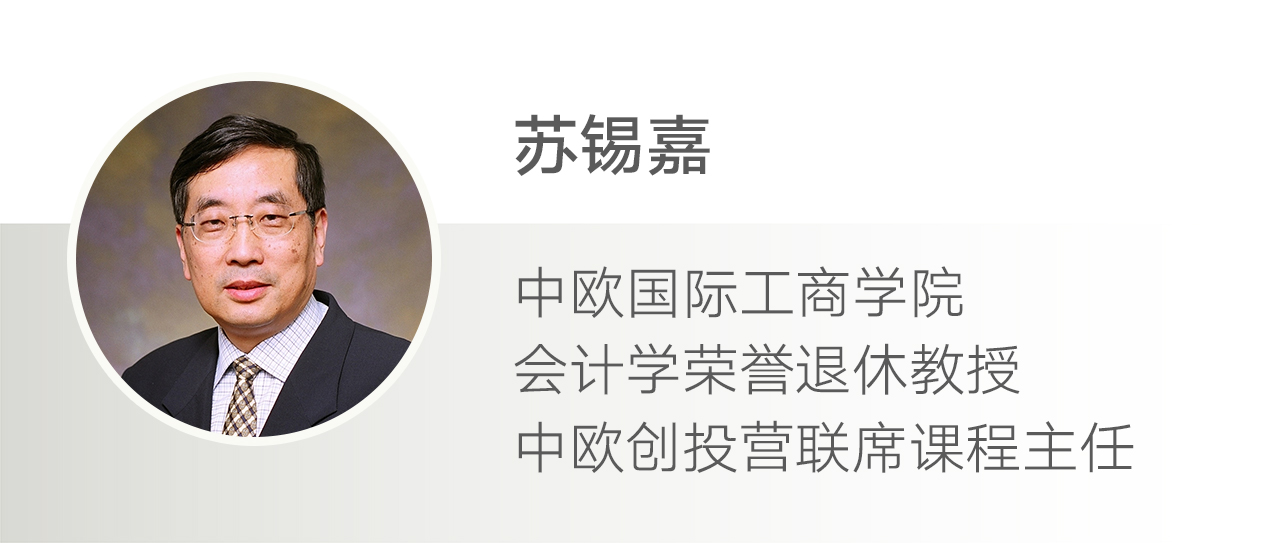
八年前我参加过类似的日本游学活动,八年后旧地重游,心中一堆疑问待解:日本有没有从“失去的30年”中走出来?中日两国企业的发展是日渐趋同,还是背道而驰?为什么人工智能的热潮中没有日本企业的影子?日本企业不着急吗?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我们开始了在日本的游学。
到日本后才了解到,许多日本企业不仅认识到自己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落伍,而且在努力分析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之道,并试图从活跃的中国企业获取经验和启发。
例如,中国在视频短剧上的成功让日本同行既不解又羡慕。中国的几家短剧头部企业,如Short Max、Drama Box、Top Short、MoboReels等都攻入了日本市场,并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其实,日本公司也拍了不少短剧,虽然拍摄水平很高,但市场反应平淡,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按拍电视剧的路数拍得短一点而已。而中国的短剧则很有技巧地在每一集中安排冲突、反转和小高潮,并以此来“勾住”观众。
为了学到短剧的精髓,著名的朝日电视台放下身段,和中国的Short Max合作,拍摄了从中国引进、改编的《保洁员竟是女总裁》。虽然是双方合作,但收入分配并不平等。据知情者透露,Short Max占据了收入的绝对大头,朝日电视台学习心态的急切隐约可见。

苏锡嘉教授为中欧创投营日本模块开场
01
产业社会VS交易社会
新的业态和模式为什么不容易在日本出现?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的高参田中信彦先生对此有十分独到的认识。他从日本政权的超长期稳定(126代天皇顺利交接班,没有发生过政权更替)和农户土地的极度匮乏谈起。日本没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土地来自封建领主,一家农户现在拥有的土地一般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块土地通常很小,土地的权属没有希望通过革命或战争得到扩展。前后左右都没有扩展余地,所以只能向上。所谓向上,无非是提高单产和改良品种,实现附加值的提升。
日本人的关注点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心无旁骛,“一生悬命,一所悬命,一意专心”就是他们的工作理念。或许是受这个理念的影响,日本人对新出现的机会和模式相对比较谨慎,甚至有些迟钝。
田中信彦先生把这种商业风格称为“产业(industry)社会”,其特点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重视公司内部履历的积累;以直营店为主来经营自有品牌;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不肯随意改变,也不愿见异思迁;主业指向,长期持续的指向;成长慢,相对安定,可以成批诞生百年企业、千年企业;与相关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分享利益。
相对应的,他将中国的商业理念归结为“交易(trade)社会”,主要特征包括:转业、改行、跳槽、并购经常发生;通过价值的转移、价值的交换来产生利润;市场指向,短期转换的指向;重视公司外部的履历;经营喜欢采用加盟店模式,既减少自己的风险,也便于快速扩大规模;高度灵活,善于为适应形势和环境而做出改变;一有机会,很多人都会做同样的事;胜者为王,胜者和败者命运截然不同。
因为中国是典型的交易社会,田中信彦先生认为中国擅长横向的拓展、跳跃、转换,快速抓住新出现的机会,但做深、做长的耐力不够。而日本恰恰相反,专注、守成、深耕。二者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问题。
他还很诚恳地指出,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日益提高,中国横向在量的方面持续扩充会越来越难。不停地寻找新的机会,既不现实,也很难带来能真正持久的利益。中国需要培育“纵向向上”的商业文化,提高商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与商业伙伴分享利益、相互提携,而不是以“你死我活”的狠劲卷到极致。对照我们的现实,似乎不无道理。

在游学的尾声,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搭新干线去往名古屋。发车时间是晚上六点左右,晚餐只能在列车上解决了。安排我们行程的校友周到地替我们定了盒饭。等我们到站台,盒饭准时送达。盒饭带自加热功能,里面的和牛是我这次在日本吃到的最好的和牛。盒饭要价7000多日元,按时送到指定的站台每盒另外收费2000多日元,加起来一盒饭差不多要合500元人民币,真心不便宜。
提供盒饭的是一个家族公司,专做盒饭已有156年的历史,公司的历史沿革被印成精美的单张,随盒饭附赠,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收费昂贵、质量上乘、服务周到、历史悠久的小公司在日本比比皆是,或许这就是产业社会最实在的例证。
比它便宜的盒饭公司或作坊即使在日本也到处都是,但它仍屹立不倒,这多少说明了日本消费者的固执,也说明了日本商业社会对稳定的合作关系的偏爱。我不禁想问:中国什么时候也能产生这样的小公司呢?或者问,要让这样的小公司在中国能够产生、生存、长寿,社会各界需要做什么?
产业社会和交易社会中的企业,因为专注度不一样,长期生存的概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日本长寿企业之多是世界闻名的。据东京大学丸川知雄教授提供的统计数据,日本125万家企业的平均寿命为40.5年,其中百年老店为19518家,200年以上的有938家,300年以上是435家。因为长期存在,员工心态极为稳定,安心钻研技术,容易培育工匠精神和精品文化。
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日本企业老态渐显,员工的主体都在40岁以上,经营风格保守稳健,缺乏冒险精神。例如,鸟取三津子女士出任日航CEO在日本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仅仅因为她是女性,因为她的学历低(大专),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女性出任大公司高管早已司空见惯。
和我们分享的日本学者和企业家一方面对日本的企业文化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对日本企业的守旧和在新科技上的少有作为感到不安。他们无一例外都对中国企业在新科技浪潮和AI研发上的突飞猛进赞不绝口。
显然,超稳定的日本企业也是有它们的短板的。进一步说,日本的创业环境并不活跃,保守的经营风格对创业企业并不友好。日本的创业企业大多非常短命,能活过5年的从来不超过5%,在百年老店层出不穷的国家显得相当无奈。

日本企业虽然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占据了极为突出的地位,但在金融、投资和高科技方面弱于欧美国家,所以整体的盈利水平低于欧美企业,中国企业就更低了。
据岛聪先生(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曾经的高参)分享,就大企业的盈利水平而言,美国企业高达8.4%,欧盟国家企业为8.2%,日本企业只有4.7%,中国企业更低至3.9%。与此相似,美国零售业企业营业利润率为5.2%,德国企业为3.7%,日本企业为4.7%,中国企业最低,只有2.5%。
低价的中国产品虽然快速征服了全世界,却也让中国企业难以摆脱低端、廉价的定位。曾经有一位中国著名家电企业的高管痛心地对我说,他们出海泰国的子公司在中国工程师帮助下生产的家电产品居然可以比中国原厂的同款产品卖得还贵。“泰国制造”比“中国制造”更能在市场上赚取溢价,说起来让人情何以堪。
我一直认为中国产品是同等价位上质量最好的,但中国产品再也不能只以低价作为主要的卖点。过度竞争卷出来的低价一方面会招来别人的抵触和反感,另一方面也难以保证产业工人的合理待遇,令年轻人不愿进工厂,进而销蚀、削弱中国制造业的长远利益。
我们在游学中特意参观了两家企业博物馆:做酱油的龟甲万和做纺织出生的丰田。两家博物馆都对公众收费开放,规模都不小,尤其是丰田。两家博物馆参观的人相当踊跃,不预约还进不来。
丰田的博物馆一半展示纺织,一半展示汽车,都极为精彩。纺织部分从一团棉花开始演示给我们看棉花怎么变成棉线,再变成纱锭和棉布。看了博物馆才知道,纺织行业的很多设备都是丰田发明的(最先进的纺织机展示现场还不允许照相),直到今天纺织还是丰田的主业之一。

中欧创投营日本游学团参访丰田企业博物馆
让年轻人愿意进工厂,从小让他们爱上工业博物馆应该是很有效的办法,不知我们的企业有多少愿意尝试。
02
日本综合商社
日本综合商社是做什么的?在我以前的印象中,综合商社就是国际贸易公司,实际上这多少是个误解。我们本次游学的分享嘉宾中有天野英介先生,原伊藤忠商事(Itochu Corporation)负责中国区业务的高管。
日本有著名的五大商社(另外四家为三菱、三井物产、丸红和住友商事),经营的业务匪夷所思地广泛。在日本,小到鸡蛋、面粉,大到矿产、石油以及火箭、卫星,都可以看到综合商社的身影,可以说综合商社就是一个产业综合体,其他国家很少有类似庞杂的企业组织。
和我们分享的伊藤忠商事在综合商社中目前排名第二,总部位于大阪,属于第一劝银财团。伊藤忠商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纤维、金属、能源与化学、食品等,其中纺织和纤维是其优势。伊藤忠商事还是日本著名的永旺百货的股东。综合商社的三大功能包括贸易、服务和投资。
理解日本经济必须先理解日本商社的作用,日本商社扮演了产业组织者的角色,让不同业态、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商社集团内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集团内的企业合作无间,对集团外的企业则百般排斥。
例如,在其他国家坐飞机,问你要喝什么,你或许会说:我要喝啤酒。但在日本,出差在外的你一定要喝你们集团出的啤酒。所以,日本的飞机上至少要备三种啤酒:朝日、札幌和麒麟,有的时候还要加三得利。日本的几大便利店,如全家、罗森、7-11,都分属于不同的商社,支付系统互不兼容。等到支付宝杀进来,因为超脱于所有的商社,反而大行其道,如今已是日本主流的支付系统之一了。
集团内互帮互助,紧密合作;集团间严防死守,不让分毫。这已成了日本商社文化的典型状态,利弊互见,相沿成习。因为规模庞大,因为财力雄厚,因为长年积累,五大商社的盈利丰厚且稳定,因此得到了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的青睐。他从2020年起陆续对五大商社都下了注,据说回报不错,看来商社这一日本独特的商业模式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03
与时俱进的日本线下商业
来日本前就听说,日本的线下商业非常兴旺,与中国线下商店的萧条不振恰成对照。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的线下商店也是甘苦两重天。
东京秋叶原的电器商店前几次来都是人潮汹涌,这次虽不至于门可罗雀,但门庭若市的热闹场景也已看不到了。能够持续兴旺的线下商店都是洞察了年轻人的需求并能与时俱进的。
我们这次听取分享并实地体验的线下商店有两家:折扣零售巨擘唐吉诃德和露营用品公司Snow Peak。
唐吉诃德最初主要销售库存尾货和临期食品,1989年开设了第一家唐吉诃德门店,正式进入折扣零售领域。截至2023年6月底,唐吉诃德在全球8个国家拥有718家门店,其中海外101家,主要分布在北美和亚洲地区。唐吉诃德最引以为豪的是38年来业绩年年增长,甚至是拿出了“经济越差我们增长越快”的魔幻业绩。
唐吉诃德24小时不间断营业,依托“便利+折扣+娱乐”的经营理念,通过高质低价的商品持续引流,带动客流量,同时销售高毛利尾货和自有产品以保持盈利。店里的营业员有充分的自主权,在划归自己管辖的那一小块店面可以自主决定采购什么、怎么布置、怎么促销等。
走进唐吉诃德,就像走进迷宫,走道狭窄,货物堆得铺天盖地,顶到天花板。在唐吉诃德逛,享受的是寻寻觅觅、不时有惊喜发现的乐趣。而且每家门店各不相同,我们去的秋叶原店,以二次元为主打元素,吸引的是年轻人。而在银座的唐吉诃德则辟出很大的面积卖奢侈品。店内的布置让你觉得这里的东西应该很便宜;确实,很多东西是便宜,但也有不少商品卖得比别人贵。到了唐吉诃德,你很难空手而归。即便像我这种对购物毫无兴趣的人也买了好几件商品。
唐吉诃德的前总经理、现任董事兼战略顾问中村好明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是如何精密分析、计算不同地段的门店在不同时段有什么样的客户,需要什么特别的商品,怎么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用心之深,观察之细,谋划之周,令人叹为观止。唐吉诃德夸下海口,今后还要继续增长几十年,2030年要实现利润2000亿日元(约人民币500亿元)。

中欧创投营日本游学团参访Snow Peak
Snow Peak是日本的顶级户外品牌,倡导“人生就是野营”,引领了日本乃至全球的户外露营风潮。不久前,该公司更是在日本开出一家功能齐全的户外主题乐园。Snow Peak旗下有25个产品品类,一系列高品质且实用性极高的产品包括帐篷、餐具、睡袋、炊具、供暖设备,等等,定位高端,被称为“露营界的LV”。Snow Peak公司总部就在露营区,出门就可以见到露营者,随时听取客户的反馈。公司总部布置得就像一个大型的露营区,提醒员工时刻保持对客户需求的敏感。
除了深耕露营产品,Snow Peak还开发了与户外生活方式相关的其他业务,包括7个自营露营地、自然生活方式度假村、商业咨询、微型房屋、房地产等。在线下的门店,营业员的职责主要不是推销,而是以露营爱好者的身份与顾客分享产品的应用场景和使用体会。
推动日本线下商业发展的底层逻辑被知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先生概括成7个S:Slow(慢悠悠,慢慢来,手工制作,传统,安全,对所有人友好);Small(小型社区关怀场所);Sociable(社交,交流);Soft(柔和、温顺、平静);Sensuous(感官满足);Sustainable(可持续);Solution of Social Problems(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环境、老龄化、性别不平等、出生率下降等)。
细想一下,日本社会的变化或多或少也正发生在中国,他们线下商业的发展思路对我们不无启发。由于中国的电商过于发达,对线下商业的生存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线下商业的兴旺对于新时代的社区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发展线下商业要有新的思路。
振兴线下实体店不能靠简单的政策扶持,不能靠大喇叭聒噪,要有制度创新。日本发展实体商业的办法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从底层逻辑出发探索可行方法的路径值得我们借鉴。
04
中企出海日本的启示
由于游学时间有限,我们没能去在日校友企业参访,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好在随团的创业营李通(中欧创业营八期)所创立的擎朗智能早已在日本经营,对中国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境遇有非常真切的感受。
擎朗智能以服务机器人为主打产品,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餐馆里的送菜机器人,大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餐厅用的都是擎朗智能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成功后,出海成了其自然的选择。
日本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更丰富,利润率也更高,但相应的技术门槛也高,安全性的标准非常严格。

擎朗智能机器人
最初,擎朗智能想把已经在中国成功的产品照搬来日本销售,但根本无人问津。仔细分析后才明白,日本餐馆的面积普遍狭小,原来在国内很好用的机器人在日本餐馆无法顺畅通行。改造后体积小、灵活度高的机器人不仅在日本大卖,还得了日本的设计大奖,上了日本当红的电视综艺节目,成了为中国产品代言的明星。
中国产的机器人在日本畅销的背后,是中国出口产品综合实力的悄然提升。李通说,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过去是以别人产品80%的性能卖50%的价格,今天已达到别人产品150%的性能,却只卖80%的价格。所以日本产的服务机器人基本已退出市场。
当然,中国企业在日本的经营还面临诸多挑战,容不得半点疏忽。例如,在日的中国企业都雇有日本员工,许多都是大学刚毕业的。他们一进公司就希望签终身合同,认为这是日本公司的惯例,但中国企业都不愿意失去用工的灵活性。中企一向没有终身合同的文化,最后都是以劳务派遣的方式解决,日本员工的不满是很容易理解的。
类似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出海日本的企业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学习、适应过程。
05
中日关系对企业的影响
最后,我想聊聊中日关系对两国企业的影响。不得不说,中日两国的关系在最近一二十年中经历了不少波折,两国民间彼此的好感程度似远不如刚恢复邦交的那段日子。近年来更不断有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传闻,两国间颇有些寒意。
但两国的企业界经过这么多年的深度合作,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格局。一方面,日本企业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也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许多中国企业的成长。
优衣库的高参田中信彦先生讲了一个故事。优衣库初创时,创始人柳井正先生为了寻找合适的业务伙伴,跑了大半个中国,与中国的初创企业共同探讨做企业的理念,先从价值观谈起,然后交流如何对待员工,如何对待供应商,如何对待竞争对手,等等。碰到理念契合的便努力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长期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和稳定,有利于技术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升,更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申洲国际的马建荣先生和晨风集团的尹国新先生就是这样成了柳井正的好朋友,这两家公司也成了优衣库始终不变的供应商,成了世界级的服装大集团。

1998年,日本发生了“优衣库热潮”的社会现象,店里的产品被疯抢,所有的到货几乎都是一售而空。有幸买到衣服的消费者翻开商标发现,原来热销的产品都是中国厂家生产的,中国公司也能生产这么好的产品,从此对中国货持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什么叫“双赢”?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虽然有起伏,有障碍,但长期而言,中国企业到日本和日本企业到中国都是两国经济发展很自然的结果。以包容的态度平常对待,或许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理性选择。
春寒料峭的东京,细雨绵绵,寒风瑟瑟。我们乘坐的大巴车驶过一个路口,但见一个约莫七八岁样子的小男孩,背着书包,身着校服,薄衫短裤,撑着伞,独自一人,蹦蹦跳跳开心地走在路上。这一情景让坐在车上的所有同学默然无语,日本人对下一代的培育方式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鼓励独立闯荡,还是娇生惯养地呵护,这两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小孩在勇于试错和抵御挫折上应该有深远的差异。年幼一代的未来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我们成年人。我们会改变吗?
部分图片由中欧创投营日本游学团供图授权。









